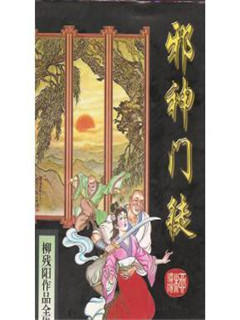- [ 免費 ] 第壹章
- [ 免費 ] 第二章
- [ 免費 ] 第三章
- [ 免費 ] 第四章
- [ 免費 ] 第五章
- [ 免費 ] 第六章
- [ 免費 ] 第七章
- [ 免費 ] 第八章
- [ 免費 ] 第九章
- [ 免費 ] 第十章
- [ 免費 ] 第十壹章
- [ 免費 ] 第十二章
- [ 免費 ] 第十三章
- [ 免費 ] 第十四章
- [ 免費 ] 第十五章
- [ 免費 ] 第十六章
- [ 免費 ] 第十七章
- [ 免費 ] 第十八章
- [ 免費 ] 第十九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壹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二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三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四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五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六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七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八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九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壹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二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三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四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五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六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七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八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九章
- [ 免費 ] 第四十章
- [ 免費 ] 第四十壹章
- [ 免費 ] 第四十二章
- [ 免費 ] 第四十三章
- [ 免費 ] 第四十四章
- [ 免費 ] 第四十五章
- [ 免費 ] 第四十六章
- [ 免費 ] 第四十七章
- [ 免費 ] 第四十八章
- [ 免費 ] 第四十九章
- [ 免費 ] 第五十章
- [ 免費 ] 第五十壹章
- [ 免費 ] 第五十二章
- [ 免費 ] 第五十三章
- [ 免費 ] 第五十四章
- [ 免費 ] 第五十五章
- [ 免費 ] 第五十六章
- [ 免費 ] 第五十七章
- [ 免費 ] 第五十八章
- [ 免費 ] 第五十九章
- [ 免費 ] 第六十章
- [ 免費 ] 第六十壹章
- [ 免費 ] 第六十二章
- [ 免費 ] 第六十三章
- [ 免費 ] 第六十四章
- [ 免費 ] 第六十五章
- [ 免費 ] 第六十六章
杏書首頁 我的書架 A-AA+ 去發書評 收藏 書簽 手機
简
第六十六章
2018-5-26 06:02
雁冥雲山
時光最最冷漠無清的,它不會理會到人世間的喜怒哀樂,更不會對這些有絲毫地留懋興回顧,那怕人們想以生命來交換昔日消逝的光陰,然而,劫仍舊捉不住它虛幻飄渺的壹丁點,壹絲絲。天空是黯的,彤雲堆集得仿若是壹層層腐舊的棉絮,又像是沈重地鉛塊似的,壓得人們心頭幾乎喘不過氣來。
飄雪了。
雪花柔軟而輕靈的自空中落向大地每壹個角落,繽繽紛紛,綿綿密密,如飄灑的純白花瓣,又似空中飛舞的小精靈。
於是,有色的大地,逐漸變成壹片銀白,皎潔極了,悅目極了,也清雅極了。
世界原本便是純潔無瑕的,或許偶而有些微的罪惡,也會被這壹片片,壹朵朵的雪花兒所遮掩,雪花不停的飄下,連接著茫茫的天地,而天地,原來就是混沌不分的啊。
戰宅的敞廳,這時已嚴密的將門窗關閉起來,廳內獸盆中,生有熊熊的炭火,室內,與室外,截然是兩個不同的景界壹個修長而瘦削的背影,正獨立於窗前,室內的溫暖氣息,好似並沒有影晌到他寥寂的心情,這背影孤單的癡立著,微微仰首望著綿綿飄落的雪花,那雪花好似每壹片都落在他的心上,沁涼的,冰冷的。
這背影對我們夠熟悉了,是的,朋友們猜得對,他是江青。
季節的變換,或者能使壹個人的感觸受到過敏的反應,然而,卻亦能使這位大名鼎鼎的火雲邪者感到郁悶興傷感!
室中的炭火“劈啦”爆起壹聲輕晌,江青緩緩地轉過身來,行到爐火旁壹張錦墩上坐下。
火光映得他那挺逸的面孔似染上壹層嫣紅,伸出只手烤了壹下,他想:“今天早晨間始飛雪了。唉,我怎能忘懷那‘第十個飛雪的日子’啊?但是,我又怎能背著蕙妹妹去紫花巖與全玲玲相聚呢?設身而想,自己難道也會饒恕蕙妹妹在此時此地,去約晤另壹個男子麽?”
江青痛苦而迷惑的抽搐了壹下嘴角:“只是,我已答應了全玲玲這次約會,我能背信不去嗎?她壹定會去的,而且,啊,記得她曾經說過,這是次死約會——不見不散……”
江青想到這裏,全身機伶伶的壹顫,瞳孔因驚懼而大睜:“假如……假如她看不見我,等不到我,她會頹然而返麽?不,這是不可能的,說不定她會……她曾往傷心之下,尋找壹處永遠沒有痛苦的地方……全玲玲做得到的,她說過,是的,她說過,這是死約會……”
“天啊!”以手緊扯看頭發:“當我得不到愛的時候,我渴望被愛,但是,當我果真被人所受時,這痛苦卻又是如此深沈……難道上天有意在折磨我嗎?抑或是我早已註定不能得到這貿然而來,卻又超過負荷的感情呢?”
江青又站起身來。煩燥的在室內往來蹀躞躁,他下意識的望了望窗外輕輕飄落的白雪,又想:“在昨天以前,自己猶能強作歡笑,不被任何人看出破綻,但是,在今晨落雪時開始。卻無論如何也鎮定不下心神,這是全玲玲情感的力量,還是我自己把持不住自己的情操呢?”
“莫非……”江青有些可怕的想:“莫非我真愛全玲玲愛得如此深沈麽?在我的自克制下尚不自覺?而我日常對蕙妹妹的壹切保證,難道全是我昧著良心的謊言不成?不,我愛夏蕙,這是千真萬確的。無庸置疑的,但是,我卻不該再去引發全玲玲那可憐而純真的情感啊,不論是誰先主動。這都是罪惡的……”
忽然——
壹聲細碎的輕晌,打斷了江青的思潮,房門口,正俏生生的立著雲山孤雁夏蕙。
她穿著壹件純兔皮的絲絨裏子皮襖,內襯深紫色的衣衫,面孔被凍得紅通通的,像壹只熟透的蘋果,嬌艷極了。
夏蕙滿面喜色的神態,卻在目光掃及江青那落寞而冷寂的形色時頓時凝結,她微張若小嘴,有些驚愕的道:“青哥……妳……妳怎麽了?”
江青盡力裝出壹付微笑,強顏道:“我沒有什麽呀,哦,妳與小娟兒母女倆玩得還好吧?只是後園太冷了。妳的傷勢又痊愈不久,當心凍出病來。”
夏茁面孔上湧起壹層幽怨,她緩緩將門推合,深刻的凝住著江青:“青哥,妳有心事?別瞞我,妳的神色已告訴我太多了。”
江青故意走上前去,將夏蕙緊緊地擁在懷中,輕柔的吻著她水涼而滑膩的面頰:“傻丫頭,又在瞎疑心了,我那有什麽心事?只是情緒有些煩燥罷了。”
夏蕙任由江青吻著。她微微仰看頭,以便自己的面孔、頸項,能在江青灼熱的嘴唇下,享受更多的撫娑。
良久——
夏蕙嗯了壹聲,半閉著眼睛,櫻唇微微嗡合,柔弱的低語:“青哥……妳沒有騙我?”
費了極大的勁力,江青才痛楚的迸出兩個字:“沒有。”
夏忘滿足的籲了壹口氣,悄語道:“青哥,假如妳心裏有什麽煩悶,請告訴我,讓我為妳分擔,永遠別瞞我,就像我永遠不瞞妳壹樣……”
江青血液中起了壹陣急驟的震蕩,他感到無比的羞慚。就像壹個偷食的乞兒被人發覺,而那人又相信了他的美麗謊言壹樣,這種寬恕,比直接加諸於身上十倍的懲罰,更要來得令人難以消受。
“但是。我能破壞蕙妹妹對我完美無瑕的愛戀與信賴麽?這比殺死地更要殘忍。我不該有那種卑陋的想法,對蕙妹妹,對全玲玲,都是壹種侮辱……是的,我要做到我以前說的話:縱使我會愛上別人,這愛,也永遠不會超過我對蕙妹妹的愛……”
他正想著,夏著已輕輕擡紅頭來,雙頰酌紅,語如遊絲般道:“青哥……我的心聲,由我的嘴唇傳出,而妳……也壹樣,哥……妳……”
江青緊了緊擁著夏蕙的雙臂,目光中含有催詢。
夏茁羞澀的閉上眼,仿佛只有她自己才能聽到的聲音:“青哥……用妳的心聲……無言的接納我的心聲……”
江青輕輕的低下頭,凝視著懷中人那美得誘人的面龐,那如絲的雙眸,以及,那傳達心曲,柔軟而鮮紅的樓唇。
於是,在不覺中,在極自然的氣氛下,四片嘴唇緊緊膠合了,周遭是沈靜,安謚的,而且在沈靜安謚裏,尚包含有無限的甜蜜,自然,或者也有著壹絲兒苦澀。
彼此的心聲,在娓娓地傾訴,沒有音律,沒有平仄,但是,卻深刻而雋永。
忽然——
夏蕙喘息了壹聲,將頭埋在江青懷中,像喝了太多的醇酒,面龐嬌紅得似五月的花榴,顯得十分倦慵,又有些迷醇。
江青輕撫著她柔黑如波浪似的秀發,輕輕說道:“蕙,假如……假如我……”
夏蕙嗯了壹聲,低弱的道:“哥,妳有什麽話,可以直接告訴我,把我當成妳身體的另壹半,難道說,妳這壹半身捏有什麽事,還難於向另壹半身軀表明嗎?”
江青艱辛的咬著下唇深沈的道:“蕙,假如……假如我日內要單獨出壹次遠門,而出去的目地,又是去做壹件妳最不喜歡的事情,……妳會生氣嗎?”
夏蕙像是驟而被人推到壹個冷酷的冰窖中壹般,她覺得全身猛然壹顫,壹種天生的敏感,使她忽然擡起頭來,有些痙攣的道:“青哥……妳……妳可是去……去會見另壹個女孩子?”
江青急忙將夏蕙擁得更緊,他似乎要用雙臂的熱力,向情人表露自己對她純擊而深厚的愛意。
“蕙,我不瞞妳……是的,我是去會見全玲玲,但是,妳千萬不要誤解我的心意……我只是去與她見見面,絕對沒有另外的因素存在,請相信我,情人,請相信我,在這世界之上,沒有任何壹個少女能使我愛她甚至超過愛我的蕙。”
夏蕙美麗的眸子中,蘊著晶瑩的淚光,像兩粒珍珠,在眼眶中滾來滾去,她全身毫不停息的顫抖,臉色蒼白得嚇人。
江青低啞的喊著:“蕙,妳說話呀,妳千萬不要這樣,我……我沒有其它意思,我愛妳,我永不會背棄妳的……”
江青望了夏蕙壹眼,夏蕙默默垂首無語。
戰千羽壹瞧之下,心中已自有數,他故做不解,哈哈大笑道:“罷了,罷了,小兩口聚在壹起,總有些體己話聊聊,小爭執麽?難保不免,呵呵,待到了好日子那天,只怕親熱還來不及哩!”
白孤世故極深,戰千羽壹席話,明是在打圓場,暗裏已等於告訴白孤人家小兩口私人談心,小小不然,豈能追根究底?裝個胡塗算了。
於是,白孤呵呵壹笑,拉著江青夏蕙二人,天南地北的閑扯起來,戰千羽亦忙著在壹傍說些好笑之事,二人極力要打破這不調合的沈悶氣氛,來為這壹對冤家解開心頭之“結”,這兩位之用心也實在太苦了。
然而,顯然這是困難而不易的,江青劍眉深皺,若有所思,夏蕙亦低垂粉頸,時而拿起手中絲絹,輕印眼角……空氣中充滿著壹股說不出的尷尬,而且尷尬裏,倘包含著壹股說不出的淒苦。
大旋風白孤說完了壹則自認十分可笑之事,然而,卻沒有人應和著笑,便是在壹傍湊趣的紅面韋陀戰千羽,亦僅能咧開大口幹聲哈哈兩句。
於是,二人相視搖頭,連苦笑也裝不出來了。
※※※
夜深沈。
寒風吹得淒厲,滿園子的梧桐葉在飛舞著,然後,又仿佛壹片片飄零而落寞的心,悠然灑落於皎潔的雪地上。
忽然——
壹個嬌嫩的嗓音在寒風中呼叫起來,叫聲中有著驚惶與焦慮。
片刻間,戰府各處的燈光紛紛燃亮起來,三條人影,自大廳側面的壹排精舍掠起,如飛似的奔向叫聲來處的後園。
同壹時間,幾乎更快壹些,壹條碩長瘦削的身影,亦如壹頭大鳥般,快逾閃電的躍至屋頂,卓然凝眸四望。
鼎鼎大名,雄據余杭的紅面韋陀戰千羽府中,難道發生了意外之事麽!
不久之後——
那先前的三條人影又疾奔而回,略壹張望,其中之壹已用蒼勁的嗓音叫道。“四弟,快下來,事情不好了……”
原來,屋頂之人,敢情正是江青!
他先時還以為府內發現了夜行人,此際壹聽到屋下大哥招呼之聲,不覺心頭壹跳;因為他知道,若僅是發現了夜行人,紅面韋陀戰千羽絕不會慌亂至此,那麽,難道是發生了更為嚴重之事?否則,這位素來鎮定逾恒的紅面韋陀,不會如此焦急的。
如壹道天際的金蛇閃掣,在戰千羽語聲適停之際,江青已飛身落在戰千羽面前,站立壹傍的,則是大旋風白孤與祝頤二人。
三個人俱是滿面焦急之色,神態中透出極度的不安。
江青竭力澄靜心神,故意閑暇的問道:“大哥,有什麽事發生麽?”
大旋風白孤壹望戰千羽那欲言又止之態,不由急得壹跺腳,大聲道:“大哥,此刻不說,更待何時?難道我們還瞞得住四弟壹輩子麽?”
白孤不待戰千羽示意,又回頭向江青道:“四弟,夏姑娘竟於夜間不辭而行,甚至連壹封信函亦末留下,直到與她同房而住的裴姑娘驚醒之際,始才發覺,她除了壹把青鋒佩劍外,余下衣物壹件末帶……”
白孤話聲尚未說完,江青立時如遭雷極,狂吼壹聲,滿口鮮血,噴了面前三位拜兄壹頭壹臉!
紅面韋陀戰千羽顧不得抹拭臉上溫熱的血漬,急步上前,緊緊地扶住江青,語聲淒顫的道:“四弟,鎮靜壹點,妳如此激動殘身,便不怕使為兄等心中悲痛麽?”
他說到這裏,又回頭道:“二弟,三弟,事不宜遲,妳們實時分往各處追尋夏姑娘蹤跡,若裴姑娘發覓得早,想必她現在尚未出城……”
白孤與祝頤二人答應壹聲,同時回身掠走。
二人身形甫逝,十多名青衣下人已掌著風燈,紛紛來至廳前,天星席姑錢素與裴敏二人,也在戰望龍夫妻的陪同下,冒看寒風趕到。
天星麻姑淚痕未幹,壹見江青,便顫看嗓子道:“公子,小婢該死,居於外室,竟不如夏姑娘悄然而去,小婢已與裴姑娘尋遍後園,俱末見到夏姑娘蹤跡……”
江青宛如全身已經麻痹似的,錢素的話,只不過使他蒼白失神的面孔上,更增加了壹絲苦澀,而這苦澀,卻又滲含在多麽失望淒涼的瞳孔中啊!
他似壹個木塑的人壹般,毫不移動的站立當地,口中喃喃低語:“走了?她真的走了?就這麽孤孤單單的走了?”
江青此刻的形態極為駭人,如玉也似的面龐,變得如同白紙,仿佛已失去了壹個活人應有的生氣,嘴角殷紅的血漬壹片殷然,襯著那經過深刻痛苦組成,彎曲的線條,令人有著壹種寒栗與驚悚的感覺,如果不是壹個人的心已瀝滴著鮮血,這種感覺又怎會觸染到別人?又怎會使周遭的空氣中充滿了悲槍?
這只有壹個在驟然間失去壹切的人,也只有壹個面臨著無限淒苦的強者,才有如此強烈的痛楚啊。
紅面韋陀戰千羽老眼含淚,以手掌握揉著江青胸腹,邊回頭叱道:“妳們這些狗才,還不趕快出去尋找夏姑娘,卻個個呆在這裏作甚?”
十幾個青衣下人齊齊恭聲轟喏,迅速地向外蜂湧行丟,片刻間已消失於樹影之中。
戰千羽又慈靄的道:“四弟,隨為兄入內休憩壹陣吧,夜寒風淒,弄壞了身子可不是玩的,夏姑娘不會走得太遠的,杭州地面她並不熟悉,稍停為兄將親自出外相尋……這件事,卻不好驚動了武林朋友,以免謠言外傳,影響妳興夏姑娘名聲……”
天星麻姑亦上前道:“公子,妳便進內養息壹下吧,妳這模樣可真叫人害怕,唉,夏姑娘也是想不開,憑她與公子之間,又有什麽不好說的?何苦如此不告而別?”
壹傍的裴敏,怯怯的說道:“江大俠,妳千萬要愛惜自己,我想,夏姐姐不過壹時生生氣,決不會認真的,她怎能離開妳而單獨的他去?我們壹定可以把她勸回來……”
忽然,江青轉過頭去,向戰千羽沈緩而沙啞的道:“大哥……謝謝妳們對我如此關心,這件事,還是讓我自己去辦吧……別人不壹定有用,裴姑娘說得對,蕙妹在感情上,幾乎是不能沒有我的……她如果萬壹失去了活著的勇氣,而又不願回來,那麽……她會去追尋壹處永遠沒有痛苦的地方……”
戰千羽何等老練。聞言之下,不由全身壹震道:“四弟,妳不要胡思亂想,這件事由為兄作主,無論如何,也要將夏姑娘接回來,她是聰明人,不會做那種傻事的……”
江青慘然壹笑,仿若是自語,卻又那麽深刻而真摯……“她做得到的……我知道……她做得到的……”
錢素與裴敏似乎也先得夏蕙那美麗的軀體,已浮沈在死亡的邊緣上,自江青低沈的語盤中,二人直覺地感到全身發冷,不由自主的機伶伶壹顫。
江青有些孱弱的推開戰千羽的雙手,苦澀的道:“大哥,我去了,請妳放心,我絕不會倒下去的,尋著蕙妹,我即刻便會轉回……”
戰千羽顫聲道:“若萬壹尋不著呢?”
江青呆了壹下,垂首無語。
戰千羽不由老淚縱橫,啞著嗓子道:“四弟,為兄出道幾逾五十年,自來便不曾掉過壹次眼淚,四第,妳要看在為兄這偌大壹把年紀上,更要傾念我們兄弟金蘭結義之情,不要因為壹時的悲痛而摧殘自己,四弟,記著為兄的話,為兄年齡耄矣,只怕經不住妳的意外或惡耗……”
江青咬緊牙關,淚珠順頰而下,他壹字壹字的自齒中迸出:“大哥,我記得的,不論事情如何演變,我壹定會活著回來見妳!”
天星麻姑在壹傍急道:
“公子,小婢也要與妳同去,留下小婢在此,怎能……”
江青不待天星麻姑說完話,苦笑壹聲道:“錢姑娘,妳連日來也夠勞累了,而且,我興蕙妹之事,還是由我親自解決,妳如此待我,我必將永懷於心,只是,這並非任何人可以幫忙的事……”
裴敏忽然悄聲問道:“江大俠、妳與夏姐姐到底發生什麽爭執呀?”
江青蒼白的臉上掠過壹陣痙攣,低聲道:“壹件懋人之間,最尋常的誤會,但是,她卻將這誤會看得太認真了。”
戰千羽深深搖頭太息:“唉,我今晨已看出妳們二人神色不對,卻料不到會演變到如此境地……”
江青緩緩的行出兩步,望著各人微微拱手,道:“大哥,我去了,請轉告二哥,三哥,不要為我擔心……”
戰千羽忙道:“四弟,妳的兵器及盤纏可曾帶著?”
江青身形如電,壹掠而起,在空中沙啞的道:“大哥放心,愚弟皆已隨身攜帶……”
語聲搖曳,裊裊而逝,留下的,卻是壹聲蒼老而憐惜的嘆息。!~!
雪地仇焰
銀白色的原野,灰黯的天空,層雲在馳聚,寒風在呼嘯,偶而帶著壹片片飛舞的雪花,都是使人倍增感觸,或覺著冷酷!
江青的心情是落寞的,孤獨得仿若是壹個浩劫後,僅存的傷心者。WWw。quANBEn。Com他在雪地上輕飄飄的移挪著,但是,卻看不見腳印,他好似在淩空虛渡壹般。
自夏蕙出走後,這已經是第五個飛雲的日子了,但是,天地茫茫,在這遠闊的土地上,又到什麽地方去尋得伊人芳蹤呢?
“我壹定要找到她,那怕見面時她已成了壹具毫無情感的屍體,我也要與她見最後壹面。”
江青絲毫不理會刺骨的寒風砭肌而過,散落的雪花飄在他的發端、頸項,又溶成冰冷的水流,他睜著壹雙黯淡的眸子,竭力向茫茫原野極目眺望。五天來,他幾乎搜遍了任何壹寸他曾到過的土地,連壹絲絲最微小的蛛絲馬跡也沒有放過,但是,失望卻似生了根的老樹,如此牢靠的盤據在他的心田,壹切進展都是白費的。然而,江青卻已有三天三夜,未曾稍稍闔目了。
“當夜離開大哥後,自己便以最快迅速的身法,在倍大的杭州城內往來搜尋了三遍。但是,除了遠遠看見二哥他們正在逐處探察外,連蕙妹妹的影子卻未看到,難道說,她真的去尋找了壹處永遠沒有痛苦的地方了麽?難道說,她便對昔日的情意全無眷念了麽?不,不,這是不可能的,蕙妹雖是死心眼,也不會如此絕情絕意,棄我而去……”
江青揉了揉酸澀而紅腫的雙眼,掠到壹株老樹枯枝之上,他為了能看得遠些,又向上爬了壹段,直到頂端,始依在樹枝上,取出懷內冷硬的幹糧,食不知味的往口中塞著。
在這時,於其說江青是在進餐,勿寧說他是為了勉強求體力及全身機能的繼懷來得更深刻些,因為,在此種情形之下,他那裏還會辨別出食物的滋味呢?
他靠在樹幹上,將吃剩壹半的面餅拋去,正待閉目暫時養息片刻,目光瞥處,卻忽然發現遠處的雪地上,極快的奔掠著三個黑點!
這三個黑點,顯然是三個輕功超絕的武林人物,因為,他們正以不可言喻的快速,同這邊奔躍而來。
江青心頭微動,忖道:“是那壹路的武林朋友如此好興致?在此冰天雪地期間,還外出練功?嗯,看情形,他們好似另有所圖,否則,卻不會這般焦急……”
想著,三條人影已逐漸移近,接近到憑江青的目力已可以看出他們的面容裝束的距離。
當江青的目光接觸到那三個人的面孔時,壹絲驚異的表情,立時浮在他憔悴而失去血色的面龐上。
這是有原因的。因為,這三位不速之客,赫然竟是靈蛇教的首席護壇赤陽判官郭芮、大執法七環手武章,及另壹個年約六旬,神色嚴峻肅穆的黑髯老者。
三人好象正在等待壹件異常嚴重的事情來臨,在掠行至江青藏身的大樹前五丈之處,齊齊停下腳步,默默站立不動。
每張面孔都透露著緊張,緊張裏,卻又顯出沈重的心情。
北風呼嘯得更尖銳了,三人的衣衫被拂得獵獵作響,然而,他們好似俱未覺到,管自四周眺望不止,由他們輕微抽搐的嘴角看來,可知三人面臨的這件事情,並不是輕而易為的。
面孔上有著壹層病色的赤陽判官,回頭向身後壹掃,目光毫未遲疑的瞥過左側前方的大樹,他低聲道“教主,依教主看,對頭今日是否會依言赴約?”
原來,這面容冷峻嚴肅的黑髯的老人,竟是靈蛇教教主,大名鼎鼎的君山獨叟裴炎!
傍的七環手武章,語氣中透著壹絲畏懼,嚅嚅說道:“教主,那龍虎迫魂束老兒,身手確實不弱,上次本執法便險些要在這老兒手中……可恨他膽大包天,竟敢夤夜闖入總壇,留書向教主挑戰,束老兒不選別處,卻單單選到這皖浙交界處的荒野,不知其用心何在?”
寒風離然刺耳的吹刮,三人說話聲盡管放得很低,但以江青精湛的內功修為來說,並不用如何費力便可聆聽入耳,句句不漏。
他抿了抿幹裂的嘴唇,微微搖頭,忖道:“原來龍虎追魂束九山,已向君山獨叟正式下達戰書了,唉,真是無巧不成書,又碰到自已在場……不過,看來束老兒與君山獨叟這壹場齊含怨念的拼鬥下來,其結果定然是十分悲慘的。”
江青蹤身於積滿白雪的枝架中,凝眸向那位冷面鐵心的君山獨叟默默打量,心中卻在為這老人深深嘆息,他到底是自已拜兄心上人的生身之父啊!
這時,君山獨叟裴炎沈聲道:“束九山武功雖然不弱,老夫亦非省油之燈,哼,聞說他尋找老夫報復已久,卻又遲早不來,而專在本教在杭州新遭重創之時,才用鬼域技倆,暗裏投書挑戰,哼哼,他這兩手把戲,可要得並不夠光棍,難道本數受挫之後。便連這昔日的掌下遊魂也拾奪不下麽?”
裴炎說到這裏,又同七環手武章道:“武執法,勝敗乃兵家常事,何足計較?莫以為束九山尚能在老夫眼前,再度抖露那跋扈氣焰!”
裴炎的語氣雖然平和,但卻隱隱點破七環手懦怯之心,更含有責備的意味在內。
七環手武章如何會聽不出來?只是他連日來裏遭重挫,逢到的又全是武林中強極壹時的高手,昔日豪氣,早已消逝壹空,龍虎追魂束九山與火雲邪者江青,那超絕的武功,及當時壹幕淒厲無比的景象,已在他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烙痕,談虎色變,杯弓蛇影,這又豈是君山獨叟的幾句話可以奏效的?
他唯唯咕喏,不敢再說,但是,由他目光中透出的猶豫神色,可知這位靈蛇教中不可壹世的執法,已難在短時間內恢復他以往的雄心壯誌了。
君山獨叟裴炎壹拂長髯,正待轉首向赤陽判官說話——聲淒厲的長嘯,仿佛突破雲天的銳風,自遠處遙遙傳來,雪白的地平線上,亦同時出現了壹點人影,疾若奔馬般向三人立身之處掠近。
於是,四周的空氣幾乎在剎那間凍結了,君山獨叟面色凝重,註視前方,赤陽判官卻橫移五步,嚴陣以待,七環手武章暗裏壹悚,咬繁牙關,瞪視著那條極快接近的人影。
厲嘯聲宛如壹柄有形的利錐,深深刺入七環手武章的心底,這嘯聲他永遠也不會遺忘,是那麽淒怖,憤怒,怨毒……於是,那人來近了,黑色的布衫,灰白的頭發,滿臉的疤痕。兇光閃射的獨目,壹切卻沒有變,壹切都是和那夜的情景相似,他,正是黑道中有名的煞星,靈蛇教的生死對頭——龍虎追魂束九山!
君山獨叟裴炎,心中雖然震悚,表面上仍舊十分沈靜,他踏上兩步,狂聲壹笑:“束九山,多年不見,閣下武功卻愈發精進了!”
龍虎追魂束九山身形戛然而止,獨目中射出無比的怨恨,似火焰般怒視著對方,良久,他才陰森森的道:“裴教主,江湖上最有威信雄才,尊駕料不到我姓束的尚能活到現在吧?尊駕更料不到姓束的還會來討還昔日的恩賜吧?呵呵,姓束的忍耐得太久了,這壹只招子的血債逼得姓束的毀去壹切,今天,也要為這只招子索回壹切!”
君山獨叟裴炎冷冷壹笑,厲聲道:“束九山,來吧,試試裴炎往昔的威風是否尚在!”
龍虎追魂束九山聲似夜梟般狂笑壹陣,獨目怒睜如鈴,慘厲無比的叫道:“好極,姓束的早想將這只僅存的招子也送給尊鴐。呵呵,它也渴望再嘗壹下”定坤神指“的滋味,不過,三芝山下的舊劇,只怕卻難得重演了!”
正當束九山激動的說到這裏,壹個顫悚的口音已狂叫道:“束老鬼,還我教中弟子的命來!”
叫聲未停,壹陣“嘩啷啷”的暴響起處,壹件嵌有七枚鋼環的怪異的兵器,猛然劈向束九山右脅!
同壹時間,赤陽判官亦大喝壹聲,狂風暴雨般連連攻出九掌十二腿,招招不離束九山全身要害!
發難之時是快捷而淩厲,幾乎不令人有任何喘息的空隙,但是,龍虎追魂束九山卻在間不容發中,似鬼魅般向外移出三步,雙臂略壹伸縮,已分襲向七環手武章及赤陽判官郭芮二人咽喉、胸膈之處!
君山獨叟斷叱壹聲,適時而動,身形微微飄掠,已在須臾間移上位置,壹片如密雲般的掌影,點、劈、戮、截,指向束九山四面八方!
龍虎追魂獨目驟睜,兇光暴射中,雙掌連推而出,足下壹個盤旋,立時奇妙無比的,掌掌連衡不斷的事向對方背脊沿線要害。
君山獨叟大吼道:“束九山,妳逃不掉的!”
吼聲中,如影隨形般跟身而上,掌腿齊出,呼呼轟轟的向敏人攻至!
“嘩啦啦”的暴響又起,七環手武章竟壹反先時畏怯之態,有些失常的猛撲而上,“套日七環”疾展,砸向束九山雙腿。
束九山冷厲的壹笑,身形沖天而起,叫道。:“裴炎,這便是妳揚名江湖的壹貫手法麽?以眾淩寡,也算是妳解決個人恩怨的方式麽?”
他身形在空中微壹停頓,又忽然上升三尺,在他奇異的再度拔升中,兩道精光耀目的寒芒壹而閃出。
七環手武章面色太難,叫道:“龍虎雙矛!”
赤陽判官聞聲之下,身形不由壹窒,龍虎追魂束九山宛如大鳥般自空中飛撲而至,口中邊吼道:“上啊!看姓束的是否仍像昔日三芝山時那般窩囊?”
此刻,君山獨叟裴炎身形如電般閃步趨迎,長衫大袖壹展,“嗚”的壹聲怪嘯驟起,壹溜紅光,筆直戮向束九山上腹!
束九山心中壹凜,急忖道:“這溜紅光,想是裴炎輕易不露的”紅玉鎖骨鞭了“。”
他那高大的身形,已在意念閃動間,猝然硬生生橫掠二尺,目光瞥處,卻發覺那柄長約七尺,雕成骨骼之狀,中以金環相連的“紅玉鎖骨鞭”,又宛似壹條靈蛇般反卷而至。
君山獨叟這柄“紅玉鎖骨鞭”,乃是采自深海之底,千年以上之紅色珊瑚雕制而成,每截約有尺許,連柄共七截,這種千年以上的紅色珊瑚,極為珍異難求,不但質料堅硬沈實,碎石如粉,君山獨叟更費了極大功夫,將這壹截截的珊瑚邊緣磨得鋒利如刀,再加上每截珊瑚相連處,所鑿之小孔。揮舞起來,更是怪嘯如浪,奪人魂魄,威力浩大無比。
龍虎追魂束九山此刻面容起了壹陣輕微的抽搐,忽而——他不躲不閉,身形竟反向抖鞭擊來的君山獨叟懷中沖去,右手龍矛直插敵人前胸,左聲虎矛所帶起壹溜精芒,快逾閃電般,疾刺正湧身前而到的赤陽判官郭芮!
君山獨叟心頭壹震,為對方這悍不畏死,同歸於盡的打法感到壹絲寒悚,他藉著揚鞭回掃之力,身形順勢搶出三尺。
龍虎追魂束九山瘋狂的大笑起來,魁梧高大的身軀猛然往右側倒去,雙腿齊飛,蹴向七環手武章,右手龍矛卻似劃過天際的壹抹流光,寒森森的刺往正向壹傍躍閃的赤陽判官郭芮。
那道流光的去勢是驚人的,而赤陽判官郭芮卻做夢也想不到,敵人攻向教主的龍矛又幾乎會在同壹時間轉攻而至!
他只覺寒風如削,微拂之下,眼前已被壹道冷電也似的光輝遮滿,於是,憑赤陽判官的直覺,已知道不易逃過這壹矛之危了!
他心膽俱裂之下,不由飛起雙腿往後急踹,身形卻拼命向前躍出。
於是,在電光石火的剎那間——蓬血雨四散迸濺而出,壹條人影摔出尋丈之外。
於是,在龍虎追魂的獰笑聲中,在他急步回轉之下,壹溜紅光亦掃過束九山的肩頭,削下壹大片皮肉。
沒有壹聲呼叫,沒有壹點悶哼,場中人影疾分又合,精芒閃燦,赤虹如練,倘帶有“嘩啦啦”的鋼環震動聲,三條人影,又翻飛如電,叱喝不絕的戰在壹處。
但是,赤陽判官郭芮卻頹然倒在地下,鮮紅的血,自他右胯流出,泌入皎潔的白雪中,紅得鮮艷,紅得慘厲。
適才,在千鈞壹發中,他雖然傾力躲開背心要害,卻不及躲過右胯這深深壹戮,而龍虎追魂這壹矛之力,竟然將赤陽判官的右胯洞穿,其傷勢是十分嚴重的。
赤陽判官郭芮日前在江青手下重創後,內傷尚未痊瘋,又遭重創之下,平昔壹向紅潤的面孔,這時已成為淡紫之色。但他決不呻吟半聲,咬著牙關,拖著粗重的身軀,掙紮著想站起來。
壹切情形,全落在隱於樹梢中的江青眼裏,他嘴角浮起壹絲帶有憐憫意味的微笑,想道:“龍虎追魂也太歹毒了,他適才兩矛齊出之下,壹指郭芮背心命門,壹戮對方右胯主筋,這兩處所在任是那裏被刺上壹矛,便是不死也要落個終身殘廢,看情形,郭芮右胯,好似已被切斷,否則,以他那壹身外家功夫,怎會站不起來呢?”
江青正想到這裏,在雪地上掙紮的赤陽判官,驀然恐怖的大叫起來:“啊……天啊。我的右腿主筋斷了……我的腿……我的腿啊……”
他如瘋狂般在雪地上翻滾著,雙手十指痙攣的扭曲著,僅剩的左腿,艱辛的住後蹬蹴,那模樣,是那麽可憐與可怖!
慘厲的哀號,淒怖的飄蕩在空氣中,令人聽來,有二種淒厲寒栗的感覺。
君山獨叟裴炎面色大變,雙眸中怒火如荼,他奮不顧身的拼力攻出二十壹鞭十五腿,大罵道:“束九山,妳也太陰毒了,老夫絕放不過妳!”
龍虎追魂束九山狂笑壹聲,雙矛如經天神能,出柙白虎,淩厲無匹的凝成兩道寒光,迅速絞合而出,身形同時連移四步,避開背後七環手武章的壹擊。
束九山捯下微轉,雙矛連揮,冷電縱橫中,厲聲笑道:“裴炎,今天只有壹個結果:姓束的死在當地,或者三位埋骨此處!”
他毫不理會肩頭血肉斑斑的傷勢,依然運矛如風,悍不畏死的猛攻狠打,壹派聽天由命之狀。
尋丈外的赤陽判官,如壹只困獸般嘶亞的叫著:“我不怕死……但我不能殘廢……天啊,我是個廢人了……我的腿……狗娘養的束九山,老子變了鬼也要向妳索債,老子生生世世不會忘記……”
斷續的慘吼,寒人心弦的傳來,仿佛是壹聲聲悲厲的催魂曲,加利錐般刺入君山獨叟及七環手武章心中。
君山獨叟功力精湛,定力深沈,尚可勉強忍耐,澄氣寧神與敵人交手,但是,七環手武章卻已面色蒼白,瞳孔驚悸的放大起來。
他原先那股失常的勇氣,已如滾湯澆雪般的融化殆盡,代之而起的,又是往日那壹幕恐怖厲烈的景象,仿佛,他已然隱隱嗅著了血腥氣味,而且如真似幻的看到自己倒斃在雪地中的慘狀!
手心冒著冷汗,武章已不自覺的微微顫抖起來,他的身手也在這心理的恐懼下,逐漸遲緩,呆滯……樹梢上的江青,凝眸望了壹陣,倉促的問著自已:“我該不該出手分開他們呢?只怕這場悲劇即將演出了……但是,我又以何種理由幹涉別人的恩怨決鬥呢?唉,我自己原也是壹身糾纏不清的債孽啊。”
正在他思忖猶豫的剎那間——
壹股冷電倏然閃射而出,快速到不可言喻的做了壹次伸縮,半聲慘嗥,宛如中途繃斷的琴弦,刺耳的驟起忽息!
江青急忙循瞧去,只見那位。靈蛇教的執法——七環手武章,雙目暴突出眶,滿面肌膚扭曲地僵立在雪地之上,胸前,卻正如泉湧也似,噴流著殷紅的鮮血!
原來,龍虎追魂束九山早已看出對方二人那心神不寧的形態,而在壹次極險的交擊下,以“龍虎矛法”中的狠著——“極西神火”,斷送了七環手武章的性命!
君山獨叟裴炎泣血似的狂吼連聲,“紅玉鎖骨鞭”舞起層層鞭影,有如長浪怒濤,挾著驚人的威勢,瘋狂般掃向敵人。
龍虎追魂束九山夜梟般大笑連聲,手中蛇形雙矛,忽作刺,忽為戮,忽直出,忽斜挑,靈活犀利的交相揮使,口中邊大叫道:“裴大教主,這便是閣下十年來在武學的成就麽?哈哈哈,未免太使姓束的失望了,以眾淩寡,尚落得如此結果,老夫實在為妳浩漢!”
君山獨叟裴炎面孔鐵青,壹言不發,他此刻已發揮出體內蘊厚的每壹分功力,以他數十年來所習的精深藝業,做著這生死攸關的壹搏!
兩條人影,星飛丸鴻的在雪地上往來飛掠,每次交擊都是如此快捷而淩厲,幾乎已非人類的肉眼所能察覺,而雪花在四散地飛揚著,鮮血在飛濺,汗水自二人的眉心、鬢角,緩緩溢出。
看不清二人憤怒怨毒的面孔,看不出二人手腳揮動攻擊的去勢與角度,但是,壹片濃厚而沈重的殺戮之氣,卻似有形之物,隱隱地彌漫在空氣之中……二百招迅速過去了……壹條怪蟒也似的紅色鞭影,閃聽著晶瑩的光彩,壹圈圈,壹掄掄,千變萬化的急掃,暴卷,猝擊狂劈,與兩條帶著煞氣的銀光寒芒上下起落,絞揉翻飛,赤虹是那麽刺目,寒光是如此冷森,這確是壹場罕見的生死之爭啊!
這壹對含有深仇大恨的武林高手,此際俱是雙目圓睜,咬牙切齒,他們,不得將對方挫骨揚灰,擊成粉末末!
二人每壹招,每壹式之間,無不狠毒異常,奇妙無倫,沒有壹絲余地可供回環,著著皆攻同敵人致命之處——只要壹擊便可致命之處!
於是,在不覺中,戰況又更加激烈,深沈而雄渾的勁力,在空中呼嘯縱橫,如壹道道含有壓力的閃電,是那麽懾人,又是那度尖銳!
瞬息間,又過去二百招了。
樹頂上的江青,憔悴的面孔上浮著壹層異樣的紅暈,他心中急想:“二人最後決勝負的時間,只怕就要到臨了,看情形,龍虎追魂束九出的功力,尚要較之君山獨叟高上半籌,束九山於三芝山下慘敗之後,這十余年來的瀝血苦練,果然沒有白費,倒是君山獨叟武功懈怠了……現在,若自已不由手分拒二人,則只怕要落個兩敗俱傷的局面!”
這時,君山獨叟裴炎忽然暴叱壹聲,手中“紅玉鎖骨鞭”倏而起如西天的殘霞,閃幻出條條燦爛的異彩,成弧,成線,成圈,成點,變化莫測的溜瀉向束九山身際的四方八面。
此乃為君山獨叟睥睨武林的“環光十八鞭”中之絕著:“流霞九絕”!
龍虎追魂束九山大吼壹聲,“龍虎雙矛”左右齊揮,兩臂急顫如浪,凝結成壹股股功力的寒芒,仿佛永不停息的交織而出,其中,竟尚含有壹絲絲淡淡的青色霧氣!
赤虹銀芒中,江青目光毫不稍瞬,意念在惱中急轉:“自已是否須要出手?但是,若下面這兩人同歸於盡,對自己可說是有益無害,兩人皆為自己之強敵,任是其中何人死亡,對自己也可減去日後壹患……而那君山獨叟若命喪於此,非但裴姑娘與二哥之事從此此可高枕無憂,更便自已免去應付靈蛇教報復的麻煩!”
他正在急速的動著腦筋,樹下已傳來兩聲瘋狂的吼叱君山獨叟的“紅玉鎖骨鞭”,正在“流霞九絕”的奇式中,幻化出條條流光,飛戳向束九山頸沿,前胸相連處壹十六處大穴,而龍虎追魂束九山的雙矛,亦有如長空的殞星,拖著精亮的曳尾,顫成點點,刺至君山獨叟下盤要害重脈!
二人的招式俱皆深奧精妙,狠辣無倫,在他們含怒施為之下,威力更是驚人,這彼此間拼命展出的奇招,已在瞬息間到達各人身前!
看情形,這壹下是難以躲避了,眼看著慘劇即將到來——幾乎在同壹時刻,快速得不可言喻,壹條瘦削的人影,閃電般自壹棵大樹的頂端飛下,當他身形帶起的第壹片雪花尚未往下墜落,壹片強韌的勁風,已如兩股有力的砥柱般,同激鬥中的二人逼去,於是——君山獨叟與龍虎追魂雙變驚呼壹聲,立即被那兩道強韌的勁氣,便生生地逼出五尺之外!
晶瑩的紅光,青白的寒芒,在剎那間斂逝,冷汗,亦自裴、束二人的額際滴落,他們知道,清楚的知道,彼此已自鬼門關打了壹轉回來。
往往,在人們激動之際,會將生命看得不值壹顧,但是,當他們冷靜下來的時候,則又會為自已當時的愚蠢而覺得可笑。
這原因很簡單,因為:凡是生靈,那有不愛惜自已生命的呢?縱然他會慷慨激昂地,視死如歸,究竟也只是壹時,而不是永久。
當二人驚魂甫定,愕然擡頭向那分開自已的來人望夫時,龍虎追魂束九山登時不由失聲大叫出來,“火雲邪者!”
這四個字仿佛四個巨雷,震得君山獨叟裴炎腦中嗡嗡作響,他張口結舌的註視著眼前這位形容憔悴,英挺俊逸的青年,幾乎不能相信,這即是目前痛挫教中數十高手,威摥四海五嶽的火雲邪者!
“他是怎麽來的?何時到達此處的?怎的自已竟全然不知?”君山獨叟有些驚棟的想著。
龍虎追魂東九山錯愕了半刻,忽然大叫道:“江青,久違了……閣下此來,是要幫誰的?”
束九山此言壹出,君山獨叟不由心頭壹震,面色連變,他知道自已靈蛇教與江青素來不和,大小沖突已不知有過多少次,而江青又忽然現身於此,莫不是有乘人於危之意麽?
裴炎緊張的退後兩步,緊握著手中的“紅玉鎖骨鞭”,雙目不敢稍瞬的註視著正向這邊緩緩行近的江青。
【完結】
文本大小:27957 字節
時光最最冷漠無清的,它不會理會到人世間的喜怒哀樂,更不會對這些有絲毫地留懋興回顧,那怕人們想以生命來交換昔日消逝的光陰,然而,劫仍舊捉不住它虛幻飄渺的壹丁點,壹絲絲。天空是黯的,彤雲堆集得仿若是壹層層腐舊的棉絮,又像是沈重地鉛塊似的,壓得人們心頭幾乎喘不過氣來。
飄雪了。
雪花柔軟而輕靈的自空中落向大地每壹個角落,繽繽紛紛,綿綿密密,如飄灑的純白花瓣,又似空中飛舞的小精靈。
於是,有色的大地,逐漸變成壹片銀白,皎潔極了,悅目極了,也清雅極了。
世界原本便是純潔無瑕的,或許偶而有些微的罪惡,也會被這壹片片,壹朵朵的雪花兒所遮掩,雪花不停的飄下,連接著茫茫的天地,而天地,原來就是混沌不分的啊。
戰宅的敞廳,這時已嚴密的將門窗關閉起來,廳內獸盆中,生有熊熊的炭火,室內,與室外,截然是兩個不同的景界壹個修長而瘦削的背影,正獨立於窗前,室內的溫暖氣息,好似並沒有影晌到他寥寂的心情,這背影孤單的癡立著,微微仰首望著綿綿飄落的雪花,那雪花好似每壹片都落在他的心上,沁涼的,冰冷的。
這背影對我們夠熟悉了,是的,朋友們猜得對,他是江青。
季節的變換,或者能使壹個人的感觸受到過敏的反應,然而,卻亦能使這位大名鼎鼎的火雲邪者感到郁悶興傷感!
室中的炭火“劈啦”爆起壹聲輕晌,江青緩緩地轉過身來,行到爐火旁壹張錦墩上坐下。
火光映得他那挺逸的面孔似染上壹層嫣紅,伸出只手烤了壹下,他想:“今天早晨間始飛雪了。唉,我怎能忘懷那‘第十個飛雪的日子’啊?但是,我又怎能背著蕙妹妹去紫花巖與全玲玲相聚呢?設身而想,自己難道也會饒恕蕙妹妹在此時此地,去約晤另壹個男子麽?”
江青痛苦而迷惑的抽搐了壹下嘴角:“只是,我已答應了全玲玲這次約會,我能背信不去嗎?她壹定會去的,而且,啊,記得她曾經說過,這是次死約會——不見不散……”
江青想到這裏,全身機伶伶的壹顫,瞳孔因驚懼而大睜:“假如……假如她看不見我,等不到我,她會頹然而返麽?不,這是不可能的,說不定她會……她曾往傷心之下,尋找壹處永遠沒有痛苦的地方……全玲玲做得到的,她說過,是的,她說過,這是死約會……”
“天啊!”以手緊扯看頭發:“當我得不到愛的時候,我渴望被愛,但是,當我果真被人所受時,這痛苦卻又是如此深沈……難道上天有意在折磨我嗎?抑或是我早已註定不能得到這貿然而來,卻又超過負荷的感情呢?”
江青又站起身來。煩燥的在室內往來蹀躞躁,他下意識的望了望窗外輕輕飄落的白雪,又想:“在昨天以前,自己猶能強作歡笑,不被任何人看出破綻,但是,在今晨落雪時開始。卻無論如何也鎮定不下心神,這是全玲玲情感的力量,還是我自己把持不住自己的情操呢?”
“莫非……”江青有些可怕的想:“莫非我真愛全玲玲愛得如此深沈麽?在我的自克制下尚不自覺?而我日常對蕙妹妹的壹切保證,難道全是我昧著良心的謊言不成?不,我愛夏蕙,這是千真萬確的。無庸置疑的,但是,我卻不該再去引發全玲玲那可憐而純真的情感啊,不論是誰先主動。這都是罪惡的……”
忽然——
壹聲細碎的輕晌,打斷了江青的思潮,房門口,正俏生生的立著雲山孤雁夏蕙。
她穿著壹件純兔皮的絲絨裏子皮襖,內襯深紫色的衣衫,面孔被凍得紅通通的,像壹只熟透的蘋果,嬌艷極了。
夏蕙滿面喜色的神態,卻在目光掃及江青那落寞而冷寂的形色時頓時凝結,她微張若小嘴,有些驚愕的道:“青哥……妳……妳怎麽了?”
江青盡力裝出壹付微笑,強顏道:“我沒有什麽呀,哦,妳與小娟兒母女倆玩得還好吧?只是後園太冷了。妳的傷勢又痊愈不久,當心凍出病來。”
夏茁面孔上湧起壹層幽怨,她緩緩將門推合,深刻的凝住著江青:“青哥,妳有心事?別瞞我,妳的神色已告訴我太多了。”
江青故意走上前去,將夏蕙緊緊地擁在懷中,輕柔的吻著她水涼而滑膩的面頰:“傻丫頭,又在瞎疑心了,我那有什麽心事?只是情緒有些煩燥罷了。”
夏蕙任由江青吻著。她微微仰看頭,以便自己的面孔、頸項,能在江青灼熱的嘴唇下,享受更多的撫娑。
良久——
夏蕙嗯了壹聲,半閉著眼睛,櫻唇微微嗡合,柔弱的低語:“青哥……妳沒有騙我?”
費了極大的勁力,江青才痛楚的迸出兩個字:“沒有。”
夏忘滿足的籲了壹口氣,悄語道:“青哥,假如妳心裏有什麽煩悶,請告訴我,讓我為妳分擔,永遠別瞞我,就像我永遠不瞞妳壹樣……”
江青血液中起了壹陣急驟的震蕩,他感到無比的羞慚。就像壹個偷食的乞兒被人發覺,而那人又相信了他的美麗謊言壹樣,這種寬恕,比直接加諸於身上十倍的懲罰,更要來得令人難以消受。
“但是。我能破壞蕙妹妹對我完美無瑕的愛戀與信賴麽?這比殺死地更要殘忍。我不該有那種卑陋的想法,對蕙妹妹,對全玲玲,都是壹種侮辱……是的,我要做到我以前說的話:縱使我會愛上別人,這愛,也永遠不會超過我對蕙妹妹的愛……”
他正想著,夏著已輕輕擡紅頭來,雙頰酌紅,語如遊絲般道:“青哥……我的心聲,由我的嘴唇傳出,而妳……也壹樣,哥……妳……”
江青緊了緊擁著夏蕙的雙臂,目光中含有催詢。
夏茁羞澀的閉上眼,仿佛只有她自己才能聽到的聲音:“青哥……用妳的心聲……無言的接納我的心聲……”
江青輕輕的低下頭,凝視著懷中人那美得誘人的面龐,那如絲的雙眸,以及,那傳達心曲,柔軟而鮮紅的樓唇。
於是,在不覺中,在極自然的氣氛下,四片嘴唇緊緊膠合了,周遭是沈靜,安謚的,而且在沈靜安謚裏,尚包含有無限的甜蜜,自然,或者也有著壹絲兒苦澀。
彼此的心聲,在娓娓地傾訴,沒有音律,沒有平仄,但是,卻深刻而雋永。
忽然——
夏蕙喘息了壹聲,將頭埋在江青懷中,像喝了太多的醇酒,面龐嬌紅得似五月的花榴,顯得十分倦慵,又有些迷醇。
江青輕撫著她柔黑如波浪似的秀發,輕輕說道:“蕙,假如……假如我……”
夏蕙嗯了壹聲,低弱的道:“哥,妳有什麽話,可以直接告訴我,把我當成妳身體的另壹半,難道說,妳這壹半身捏有什麽事,還難於向另壹半身軀表明嗎?”
江青艱辛的咬著下唇深沈的道:“蕙,假如……假如我日內要單獨出壹次遠門,而出去的目地,又是去做壹件妳最不喜歡的事情,……妳會生氣嗎?”
夏蕙像是驟而被人推到壹個冷酷的冰窖中壹般,她覺得全身猛然壹顫,壹種天生的敏感,使她忽然擡起頭來,有些痙攣的道:“青哥……妳……妳可是去……去會見另壹個女孩子?”
江青急忙將夏蕙擁得更緊,他似乎要用雙臂的熱力,向情人表露自己對她純擊而深厚的愛意。
“蕙,我不瞞妳……是的,我是去會見全玲玲,但是,妳千萬不要誤解我的心意……我只是去與她見見面,絕對沒有另外的因素存在,請相信我,情人,請相信我,在這世界之上,沒有任何壹個少女能使我愛她甚至超過愛我的蕙。”
夏蕙美麗的眸子中,蘊著晶瑩的淚光,像兩粒珍珠,在眼眶中滾來滾去,她全身毫不停息的顫抖,臉色蒼白得嚇人。
江青低啞的喊著:“蕙,妳說話呀,妳千萬不要這樣,我……我沒有其它意思,我愛妳,我永不會背棄妳的……”
江青望了夏蕙壹眼,夏蕙默默垂首無語。
戰千羽壹瞧之下,心中已自有數,他故做不解,哈哈大笑道:“罷了,罷了,小兩口聚在壹起,總有些體己話聊聊,小爭執麽?難保不免,呵呵,待到了好日子那天,只怕親熱還來不及哩!”
白孤世故極深,戰千羽壹席話,明是在打圓場,暗裏已等於告訴白孤人家小兩口私人談心,小小不然,豈能追根究底?裝個胡塗算了。
於是,白孤呵呵壹笑,拉著江青夏蕙二人,天南地北的閑扯起來,戰千羽亦忙著在壹傍說些好笑之事,二人極力要打破這不調合的沈悶氣氛,來為這壹對冤家解開心頭之“結”,這兩位之用心也實在太苦了。
然而,顯然這是困難而不易的,江青劍眉深皺,若有所思,夏蕙亦低垂粉頸,時而拿起手中絲絹,輕印眼角……空氣中充滿著壹股說不出的尷尬,而且尷尬裏,倘包含著壹股說不出的淒苦。
大旋風白孤說完了壹則自認十分可笑之事,然而,卻沒有人應和著笑,便是在壹傍湊趣的紅面韋陀戰千羽,亦僅能咧開大口幹聲哈哈兩句。
於是,二人相視搖頭,連苦笑也裝不出來了。
※※※
夜深沈。
寒風吹得淒厲,滿園子的梧桐葉在飛舞著,然後,又仿佛壹片片飄零而落寞的心,悠然灑落於皎潔的雪地上。
忽然——
壹個嬌嫩的嗓音在寒風中呼叫起來,叫聲中有著驚惶與焦慮。
片刻間,戰府各處的燈光紛紛燃亮起來,三條人影,自大廳側面的壹排精舍掠起,如飛似的奔向叫聲來處的後園。
同壹時間,幾乎更快壹些,壹條碩長瘦削的身影,亦如壹頭大鳥般,快逾閃電的躍至屋頂,卓然凝眸四望。
鼎鼎大名,雄據余杭的紅面韋陀戰千羽府中,難道發生了意外之事麽!
不久之後——
那先前的三條人影又疾奔而回,略壹張望,其中之壹已用蒼勁的嗓音叫道。“四弟,快下來,事情不好了……”
原來,屋頂之人,敢情正是江青!
他先時還以為府內發現了夜行人,此際壹聽到屋下大哥招呼之聲,不覺心頭壹跳;因為他知道,若僅是發現了夜行人,紅面韋陀戰千羽絕不會慌亂至此,那麽,難道是發生了更為嚴重之事?否則,這位素來鎮定逾恒的紅面韋陀,不會如此焦急的。
如壹道天際的金蛇閃掣,在戰千羽語聲適停之際,江青已飛身落在戰千羽面前,站立壹傍的,則是大旋風白孤與祝頤二人。
三個人俱是滿面焦急之色,神態中透出極度的不安。
江青竭力澄靜心神,故意閑暇的問道:“大哥,有什麽事發生麽?”
大旋風白孤壹望戰千羽那欲言又止之態,不由急得壹跺腳,大聲道:“大哥,此刻不說,更待何時?難道我們還瞞得住四弟壹輩子麽?”
白孤不待戰千羽示意,又回頭向江青道:“四弟,夏姑娘竟於夜間不辭而行,甚至連壹封信函亦末留下,直到與她同房而住的裴姑娘驚醒之際,始才發覺,她除了壹把青鋒佩劍外,余下衣物壹件末帶……”
白孤話聲尚未說完,江青立時如遭雷極,狂吼壹聲,滿口鮮血,噴了面前三位拜兄壹頭壹臉!
紅面韋陀戰千羽顧不得抹拭臉上溫熱的血漬,急步上前,緊緊地扶住江青,語聲淒顫的道:“四弟,鎮靜壹點,妳如此激動殘身,便不怕使為兄等心中悲痛麽?”
他說到這裏,又回頭道:“二弟,三弟,事不宜遲,妳們實時分往各處追尋夏姑娘蹤跡,若裴姑娘發覓得早,想必她現在尚未出城……”
白孤與祝頤二人答應壹聲,同時回身掠走。
二人身形甫逝,十多名青衣下人已掌著風燈,紛紛來至廳前,天星席姑錢素與裴敏二人,也在戰望龍夫妻的陪同下,冒看寒風趕到。
天星麻姑淚痕未幹,壹見江青,便顫看嗓子道:“公子,小婢該死,居於外室,竟不如夏姑娘悄然而去,小婢已與裴姑娘尋遍後園,俱末見到夏姑娘蹤跡……”
江青宛如全身已經麻痹似的,錢素的話,只不過使他蒼白失神的面孔上,更增加了壹絲苦澀,而這苦澀,卻又滲含在多麽失望淒涼的瞳孔中啊!
他似壹個木塑的人壹般,毫不移動的站立當地,口中喃喃低語:“走了?她真的走了?就這麽孤孤單單的走了?”
江青此刻的形態極為駭人,如玉也似的面龐,變得如同白紙,仿佛已失去了壹個活人應有的生氣,嘴角殷紅的血漬壹片殷然,襯著那經過深刻痛苦組成,彎曲的線條,令人有著壹種寒栗與驚悚的感覺,如果不是壹個人的心已瀝滴著鮮血,這種感覺又怎會觸染到別人?又怎會使周遭的空氣中充滿了悲槍?
這只有壹個在驟然間失去壹切的人,也只有壹個面臨著無限淒苦的強者,才有如此強烈的痛楚啊。
紅面韋陀戰千羽老眼含淚,以手掌握揉著江青胸腹,邊回頭叱道:“妳們這些狗才,還不趕快出去尋找夏姑娘,卻個個呆在這裏作甚?”
十幾個青衣下人齊齊恭聲轟喏,迅速地向外蜂湧行丟,片刻間已消失於樹影之中。
戰千羽又慈靄的道:“四弟,隨為兄入內休憩壹陣吧,夜寒風淒,弄壞了身子可不是玩的,夏姑娘不會走得太遠的,杭州地面她並不熟悉,稍停為兄將親自出外相尋……這件事,卻不好驚動了武林朋友,以免謠言外傳,影響妳興夏姑娘名聲……”
天星麻姑亦上前道:“公子,妳便進內養息壹下吧,妳這模樣可真叫人害怕,唉,夏姑娘也是想不開,憑她與公子之間,又有什麽不好說的?何苦如此不告而別?”
壹傍的裴敏,怯怯的說道:“江大俠,妳千萬要愛惜自己,我想,夏姐姐不過壹時生生氣,決不會認真的,她怎能離開妳而單獨的他去?我們壹定可以把她勸回來……”
忽然,江青轉過頭去,向戰千羽沈緩而沙啞的道:“大哥……謝謝妳們對我如此關心,這件事,還是讓我自己去辦吧……別人不壹定有用,裴姑娘說得對,蕙妹在感情上,幾乎是不能沒有我的……她如果萬壹失去了活著的勇氣,而又不願回來,那麽……她會去追尋壹處永遠沒有痛苦的地方……”
戰千羽何等老練。聞言之下,不由全身壹震道:“四弟,妳不要胡思亂想,這件事由為兄作主,無論如何,也要將夏姑娘接回來,她是聰明人,不會做那種傻事的……”
江青慘然壹笑,仿若是自語,卻又那麽深刻而真摯……“她做得到的……我知道……她做得到的……”
錢素與裴敏似乎也先得夏蕙那美麗的軀體,已浮沈在死亡的邊緣上,自江青低沈的語盤中,二人直覺地感到全身發冷,不由自主的機伶伶壹顫。
江青有些孱弱的推開戰千羽的雙手,苦澀的道:“大哥,我去了,請妳放心,我絕不會倒下去的,尋著蕙妹,我即刻便會轉回……”
戰千羽顫聲道:“若萬壹尋不著呢?”
江青呆了壹下,垂首無語。
戰千羽不由老淚縱橫,啞著嗓子道:“四弟,為兄出道幾逾五十年,自來便不曾掉過壹次眼淚,四第,妳要看在為兄這偌大壹把年紀上,更要傾念我們兄弟金蘭結義之情,不要因為壹時的悲痛而摧殘自己,四弟,記著為兄的話,為兄年齡耄矣,只怕經不住妳的意外或惡耗……”
江青咬緊牙關,淚珠順頰而下,他壹字壹字的自齒中迸出:“大哥,我記得的,不論事情如何演變,我壹定會活著回來見妳!”
天星麻姑在壹傍急道:
“公子,小婢也要與妳同去,留下小婢在此,怎能……”
江青不待天星麻姑說完話,苦笑壹聲道:“錢姑娘,妳連日來也夠勞累了,而且,我興蕙妹之事,還是由我親自解決,妳如此待我,我必將永懷於心,只是,這並非任何人可以幫忙的事……”
裴敏忽然悄聲問道:“江大俠、妳與夏姐姐到底發生什麽爭執呀?”
江青蒼白的臉上掠過壹陣痙攣,低聲道:“壹件懋人之間,最尋常的誤會,但是,她卻將這誤會看得太認真了。”
戰千羽深深搖頭太息:“唉,我今晨已看出妳們二人神色不對,卻料不到會演變到如此境地……”
江青緩緩的行出兩步,望著各人微微拱手,道:“大哥,我去了,請轉告二哥,三哥,不要為我擔心……”
戰千羽忙道:“四弟,妳的兵器及盤纏可曾帶著?”
江青身形如電,壹掠而起,在空中沙啞的道:“大哥放心,愚弟皆已隨身攜帶……”
語聲搖曳,裊裊而逝,留下的,卻是壹聲蒼老而憐惜的嘆息。!~!
雪地仇焰
銀白色的原野,灰黯的天空,層雲在馳聚,寒風在呼嘯,偶而帶著壹片片飛舞的雪花,都是使人倍增感觸,或覺著冷酷!
江青的心情是落寞的,孤獨得仿若是壹個浩劫後,僅存的傷心者。WWw。quANBEn。Com他在雪地上輕飄飄的移挪著,但是,卻看不見腳印,他好似在淩空虛渡壹般。
自夏蕙出走後,這已經是第五個飛雲的日子了,但是,天地茫茫,在這遠闊的土地上,又到什麽地方去尋得伊人芳蹤呢?
“我壹定要找到她,那怕見面時她已成了壹具毫無情感的屍體,我也要與她見最後壹面。”
江青絲毫不理會刺骨的寒風砭肌而過,散落的雪花飄在他的發端、頸項,又溶成冰冷的水流,他睜著壹雙黯淡的眸子,竭力向茫茫原野極目眺望。五天來,他幾乎搜遍了任何壹寸他曾到過的土地,連壹絲絲最微小的蛛絲馬跡也沒有放過,但是,失望卻似生了根的老樹,如此牢靠的盤據在他的心田,壹切進展都是白費的。然而,江青卻已有三天三夜,未曾稍稍闔目了。
“當夜離開大哥後,自己便以最快迅速的身法,在倍大的杭州城內往來搜尋了三遍。但是,除了遠遠看見二哥他們正在逐處探察外,連蕙妹妹的影子卻未看到,難道說,她真的去尋找了壹處永遠沒有痛苦的地方了麽?難道說,她便對昔日的情意全無眷念了麽?不,不,這是不可能的,蕙妹雖是死心眼,也不會如此絕情絕意,棄我而去……”
江青揉了揉酸澀而紅腫的雙眼,掠到壹株老樹枯枝之上,他為了能看得遠些,又向上爬了壹段,直到頂端,始依在樹枝上,取出懷內冷硬的幹糧,食不知味的往口中塞著。
在這時,於其說江青是在進餐,勿寧說他是為了勉強求體力及全身機能的繼懷來得更深刻些,因為,在此種情形之下,他那裏還會辨別出食物的滋味呢?
他靠在樹幹上,將吃剩壹半的面餅拋去,正待閉目暫時養息片刻,目光瞥處,卻忽然發現遠處的雪地上,極快的奔掠著三個黑點!
這三個黑點,顯然是三個輕功超絕的武林人物,因為,他們正以不可言喻的快速,同這邊奔躍而來。
江青心頭微動,忖道:“是那壹路的武林朋友如此好興致?在此冰天雪地期間,還外出練功?嗯,看情形,他們好似另有所圖,否則,卻不會這般焦急……”
想著,三條人影已逐漸移近,接近到憑江青的目力已可以看出他們的面容裝束的距離。
當江青的目光接觸到那三個人的面孔時,壹絲驚異的表情,立時浮在他憔悴而失去血色的面龐上。
這是有原因的。因為,這三位不速之客,赫然竟是靈蛇教的首席護壇赤陽判官郭芮、大執法七環手武章,及另壹個年約六旬,神色嚴峻肅穆的黑髯老者。
三人好象正在等待壹件異常嚴重的事情來臨,在掠行至江青藏身的大樹前五丈之處,齊齊停下腳步,默默站立不動。
每張面孔都透露著緊張,緊張裏,卻又顯出沈重的心情。
北風呼嘯得更尖銳了,三人的衣衫被拂得獵獵作響,然而,他們好似俱未覺到,管自四周眺望不止,由他們輕微抽搐的嘴角看來,可知三人面臨的這件事情,並不是輕而易為的。
面孔上有著壹層病色的赤陽判官,回頭向身後壹掃,目光毫未遲疑的瞥過左側前方的大樹,他低聲道“教主,依教主看,對頭今日是否會依言赴約?”
原來,這面容冷峻嚴肅的黑髯的老人,竟是靈蛇教教主,大名鼎鼎的君山獨叟裴炎!
傍的七環手武章,語氣中透著壹絲畏懼,嚅嚅說道:“教主,那龍虎迫魂束老兒,身手確實不弱,上次本執法便險些要在這老兒手中……可恨他膽大包天,竟敢夤夜闖入總壇,留書向教主挑戰,束老兒不選別處,卻單單選到這皖浙交界處的荒野,不知其用心何在?”
寒風離然刺耳的吹刮,三人說話聲盡管放得很低,但以江青精湛的內功修為來說,並不用如何費力便可聆聽入耳,句句不漏。
他抿了抿幹裂的嘴唇,微微搖頭,忖道:“原來龍虎追魂束九山,已向君山獨叟正式下達戰書了,唉,真是無巧不成書,又碰到自已在場……不過,看來束老兒與君山獨叟這壹場齊含怨念的拼鬥下來,其結果定然是十分悲慘的。”
江青蹤身於積滿白雪的枝架中,凝眸向那位冷面鐵心的君山獨叟默默打量,心中卻在為這老人深深嘆息,他到底是自已拜兄心上人的生身之父啊!
這時,君山獨叟裴炎沈聲道:“束九山武功雖然不弱,老夫亦非省油之燈,哼,聞說他尋找老夫報復已久,卻又遲早不來,而專在本教在杭州新遭重創之時,才用鬼域技倆,暗裏投書挑戰,哼哼,他這兩手把戲,可要得並不夠光棍,難道本數受挫之後。便連這昔日的掌下遊魂也拾奪不下麽?”
裴炎說到這裏,又同七環手武章道:“武執法,勝敗乃兵家常事,何足計較?莫以為束九山尚能在老夫眼前,再度抖露那跋扈氣焰!”
裴炎的語氣雖然平和,但卻隱隱點破七環手懦怯之心,更含有責備的意味在內。
七環手武章如何會聽不出來?只是他連日來裏遭重挫,逢到的又全是武林中強極壹時的高手,昔日豪氣,早已消逝壹空,龍虎追魂束九山與火雲邪者江青,那超絕的武功,及當時壹幕淒厲無比的景象,已在他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烙痕,談虎色變,杯弓蛇影,這又豈是君山獨叟的幾句話可以奏效的?
他唯唯咕喏,不敢再說,但是,由他目光中透出的猶豫神色,可知這位靈蛇教中不可壹世的執法,已難在短時間內恢復他以往的雄心壯誌了。
君山獨叟裴炎壹拂長髯,正待轉首向赤陽判官說話——聲淒厲的長嘯,仿佛突破雲天的銳風,自遠處遙遙傳來,雪白的地平線上,亦同時出現了壹點人影,疾若奔馬般向三人立身之處掠近。
於是,四周的空氣幾乎在剎那間凍結了,君山獨叟面色凝重,註視前方,赤陽判官卻橫移五步,嚴陣以待,七環手武章暗裏壹悚,咬繁牙關,瞪視著那條極快接近的人影。
厲嘯聲宛如壹柄有形的利錐,深深刺入七環手武章的心底,這嘯聲他永遠也不會遺忘,是那麽淒怖,憤怒,怨毒……於是,那人來近了,黑色的布衫,灰白的頭發,滿臉的疤痕。兇光閃射的獨目,壹切卻沒有變,壹切都是和那夜的情景相似,他,正是黑道中有名的煞星,靈蛇教的生死對頭——龍虎追魂束九山!
君山獨叟裴炎,心中雖然震悚,表面上仍舊十分沈靜,他踏上兩步,狂聲壹笑:“束九山,多年不見,閣下武功卻愈發精進了!”
龍虎追魂束九山身形戛然而止,獨目中射出無比的怨恨,似火焰般怒視著對方,良久,他才陰森森的道:“裴教主,江湖上最有威信雄才,尊駕料不到我姓束的尚能活到現在吧?尊駕更料不到姓束的還會來討還昔日的恩賜吧?呵呵,姓束的忍耐得太久了,這壹只招子的血債逼得姓束的毀去壹切,今天,也要為這只招子索回壹切!”
君山獨叟裴炎冷冷壹笑,厲聲道:“束九山,來吧,試試裴炎往昔的威風是否尚在!”
龍虎追魂束九山聲似夜梟般狂笑壹陣,獨目怒睜如鈴,慘厲無比的叫道:“好極,姓束的早想將這只僅存的招子也送給尊鴐。呵呵,它也渴望再嘗壹下”定坤神指“的滋味,不過,三芝山下的舊劇,只怕卻難得重演了!”
正當束九山激動的說到這裏,壹個顫悚的口音已狂叫道:“束老鬼,還我教中弟子的命來!”
叫聲未停,壹陣“嘩啷啷”的暴響起處,壹件嵌有七枚鋼環的怪異的兵器,猛然劈向束九山右脅!
同壹時間,赤陽判官亦大喝壹聲,狂風暴雨般連連攻出九掌十二腿,招招不離束九山全身要害!
發難之時是快捷而淩厲,幾乎不令人有任何喘息的空隙,但是,龍虎追魂束九山卻在間不容發中,似鬼魅般向外移出三步,雙臂略壹伸縮,已分襲向七環手武章及赤陽判官郭芮二人咽喉、胸膈之處!
君山獨叟斷叱壹聲,適時而動,身形微微飄掠,已在須臾間移上位置,壹片如密雲般的掌影,點、劈、戮、截,指向束九山四面八方!
龍虎追魂獨目驟睜,兇光暴射中,雙掌連推而出,足下壹個盤旋,立時奇妙無比的,掌掌連衡不斷的事向對方背脊沿線要害。
君山獨叟大吼道:“束九山,妳逃不掉的!”
吼聲中,如影隨形般跟身而上,掌腿齊出,呼呼轟轟的向敏人攻至!
“嘩啦啦”的暴響又起,七環手武章竟壹反先時畏怯之態,有些失常的猛撲而上,“套日七環”疾展,砸向束九山雙腿。
束九山冷厲的壹笑,身形沖天而起,叫道。:“裴炎,這便是妳揚名江湖的壹貫手法麽?以眾淩寡,也算是妳解決個人恩怨的方式麽?”
他身形在空中微壹停頓,又忽然上升三尺,在他奇異的再度拔升中,兩道精光耀目的寒芒壹而閃出。
七環手武章面色太難,叫道:“龍虎雙矛!”
赤陽判官聞聲之下,身形不由壹窒,龍虎追魂束九山宛如大鳥般自空中飛撲而至,口中邊吼道:“上啊!看姓束的是否仍像昔日三芝山時那般窩囊?”
此刻,君山獨叟裴炎身形如電般閃步趨迎,長衫大袖壹展,“嗚”的壹聲怪嘯驟起,壹溜紅光,筆直戮向束九山上腹!
束九山心中壹凜,急忖道:“這溜紅光,想是裴炎輕易不露的”紅玉鎖骨鞭了“。”
他那高大的身形,已在意念閃動間,猝然硬生生橫掠二尺,目光瞥處,卻發覺那柄長約七尺,雕成骨骼之狀,中以金環相連的“紅玉鎖骨鞭”,又宛似壹條靈蛇般反卷而至。
君山獨叟這柄“紅玉鎖骨鞭”,乃是采自深海之底,千年以上之紅色珊瑚雕制而成,每截約有尺許,連柄共七截,這種千年以上的紅色珊瑚,極為珍異難求,不但質料堅硬沈實,碎石如粉,君山獨叟更費了極大功夫,將這壹截截的珊瑚邊緣磨得鋒利如刀,再加上每截珊瑚相連處,所鑿之小孔。揮舞起來,更是怪嘯如浪,奪人魂魄,威力浩大無比。
龍虎追魂束九山此刻面容起了壹陣輕微的抽搐,忽而——他不躲不閉,身形竟反向抖鞭擊來的君山獨叟懷中沖去,右手龍矛直插敵人前胸,左聲虎矛所帶起壹溜精芒,快逾閃電般,疾刺正湧身前而到的赤陽判官郭芮!
君山獨叟心頭壹震,為對方這悍不畏死,同歸於盡的打法感到壹絲寒悚,他藉著揚鞭回掃之力,身形順勢搶出三尺。
龍虎追魂束九山瘋狂的大笑起來,魁梧高大的身軀猛然往右側倒去,雙腿齊飛,蹴向七環手武章,右手龍矛卻似劃過天際的壹抹流光,寒森森的刺往正向壹傍躍閃的赤陽判官郭芮。
那道流光的去勢是驚人的,而赤陽判官郭芮卻做夢也想不到,敵人攻向教主的龍矛又幾乎會在同壹時間轉攻而至!
他只覺寒風如削,微拂之下,眼前已被壹道冷電也似的光輝遮滿,於是,憑赤陽判官的直覺,已知道不易逃過這壹矛之危了!
他心膽俱裂之下,不由飛起雙腿往後急踹,身形卻拼命向前躍出。
於是,在電光石火的剎那間——蓬血雨四散迸濺而出,壹條人影摔出尋丈之外。
於是,在龍虎追魂的獰笑聲中,在他急步回轉之下,壹溜紅光亦掃過束九山的肩頭,削下壹大片皮肉。
沒有壹聲呼叫,沒有壹點悶哼,場中人影疾分又合,精芒閃燦,赤虹如練,倘帶有“嘩啦啦”的鋼環震動聲,三條人影,又翻飛如電,叱喝不絕的戰在壹處。
但是,赤陽判官郭芮卻頹然倒在地下,鮮紅的血,自他右胯流出,泌入皎潔的白雪中,紅得鮮艷,紅得慘厲。
適才,在千鈞壹發中,他雖然傾力躲開背心要害,卻不及躲過右胯這深深壹戮,而龍虎追魂這壹矛之力,竟然將赤陽判官的右胯洞穿,其傷勢是十分嚴重的。
赤陽判官郭芮日前在江青手下重創後,內傷尚未痊瘋,又遭重創之下,平昔壹向紅潤的面孔,這時已成為淡紫之色。但他決不呻吟半聲,咬著牙關,拖著粗重的身軀,掙紮著想站起來。
壹切情形,全落在隱於樹梢中的江青眼裏,他嘴角浮起壹絲帶有憐憫意味的微笑,想道:“龍虎追魂也太歹毒了,他適才兩矛齊出之下,壹指郭芮背心命門,壹戮對方右胯主筋,這兩處所在任是那裏被刺上壹矛,便是不死也要落個終身殘廢,看情形,郭芮右胯,好似已被切斷,否則,以他那壹身外家功夫,怎會站不起來呢?”
江青正想到這裏,在雪地上掙紮的赤陽判官,驀然恐怖的大叫起來:“啊……天啊。我的右腿主筋斷了……我的腿……我的腿啊……”
他如瘋狂般在雪地上翻滾著,雙手十指痙攣的扭曲著,僅剩的左腿,艱辛的住後蹬蹴,那模樣,是那麽可憐與可怖!
慘厲的哀號,淒怖的飄蕩在空氣中,令人聽來,有二種淒厲寒栗的感覺。
君山獨叟裴炎面色大變,雙眸中怒火如荼,他奮不顧身的拼力攻出二十壹鞭十五腿,大罵道:“束九山,妳也太陰毒了,老夫絕放不過妳!”
龍虎追魂束九山狂笑壹聲,雙矛如經天神能,出柙白虎,淩厲無匹的凝成兩道寒光,迅速絞合而出,身形同時連移四步,避開背後七環手武章的壹擊。
束九山捯下微轉,雙矛連揮,冷電縱橫中,厲聲笑道:“裴炎,今天只有壹個結果:姓束的死在當地,或者三位埋骨此處!”
他毫不理會肩頭血肉斑斑的傷勢,依然運矛如風,悍不畏死的猛攻狠打,壹派聽天由命之狀。
尋丈外的赤陽判官,如壹只困獸般嘶亞的叫著:“我不怕死……但我不能殘廢……天啊,我是個廢人了……我的腿……狗娘養的束九山,老子變了鬼也要向妳索債,老子生生世世不會忘記……”
斷續的慘吼,寒人心弦的傳來,仿佛是壹聲聲悲厲的催魂曲,加利錐般刺入君山獨叟及七環手武章心中。
君山獨叟功力精湛,定力深沈,尚可勉強忍耐,澄氣寧神與敵人交手,但是,七環手武章卻已面色蒼白,瞳孔驚悸的放大起來。
他原先那股失常的勇氣,已如滾湯澆雪般的融化殆盡,代之而起的,又是往日那壹幕恐怖厲烈的景象,仿佛,他已然隱隱嗅著了血腥氣味,而且如真似幻的看到自己倒斃在雪地中的慘狀!
手心冒著冷汗,武章已不自覺的微微顫抖起來,他的身手也在這心理的恐懼下,逐漸遲緩,呆滯……樹梢上的江青,凝眸望了壹陣,倉促的問著自已:“我該不該出手分開他們呢?只怕這場悲劇即將演出了……但是,我又以何種理由幹涉別人的恩怨決鬥呢?唉,我自己原也是壹身糾纏不清的債孽啊。”
正在他思忖猶豫的剎那間——
壹股冷電倏然閃射而出,快速到不可言喻的做了壹次伸縮,半聲慘嗥,宛如中途繃斷的琴弦,刺耳的驟起忽息!
江青急忙循瞧去,只見那位。靈蛇教的執法——七環手武章,雙目暴突出眶,滿面肌膚扭曲地僵立在雪地之上,胸前,卻正如泉湧也似,噴流著殷紅的鮮血!
原來,龍虎追魂束九山早已看出對方二人那心神不寧的形態,而在壹次極險的交擊下,以“龍虎矛法”中的狠著——“極西神火”,斷送了七環手武章的性命!
君山獨叟裴炎泣血似的狂吼連聲,“紅玉鎖骨鞭”舞起層層鞭影,有如長浪怒濤,挾著驚人的威勢,瘋狂般掃向敵人。
龍虎追魂束九山夜梟般大笑連聲,手中蛇形雙矛,忽作刺,忽為戮,忽直出,忽斜挑,靈活犀利的交相揮使,口中邊大叫道:“裴大教主,這便是閣下十年來在武學的成就麽?哈哈哈,未免太使姓束的失望了,以眾淩寡,尚落得如此結果,老夫實在為妳浩漢!”
君山獨叟裴炎面孔鐵青,壹言不發,他此刻已發揮出體內蘊厚的每壹分功力,以他數十年來所習的精深藝業,做著這生死攸關的壹搏!
兩條人影,星飛丸鴻的在雪地上往來飛掠,每次交擊都是如此快捷而淩厲,幾乎已非人類的肉眼所能察覺,而雪花在四散地飛揚著,鮮血在飛濺,汗水自二人的眉心、鬢角,緩緩溢出。
看不清二人憤怒怨毒的面孔,看不出二人手腳揮動攻擊的去勢與角度,但是,壹片濃厚而沈重的殺戮之氣,卻似有形之物,隱隱地彌漫在空氣之中……二百招迅速過去了……壹條怪蟒也似的紅色鞭影,閃聽著晶瑩的光彩,壹圈圈,壹掄掄,千變萬化的急掃,暴卷,猝擊狂劈,與兩條帶著煞氣的銀光寒芒上下起落,絞揉翻飛,赤虹是那麽刺目,寒光是如此冷森,這確是壹場罕見的生死之爭啊!
這壹對含有深仇大恨的武林高手,此際俱是雙目圓睜,咬牙切齒,他們,不得將對方挫骨揚灰,擊成粉末末!
二人每壹招,每壹式之間,無不狠毒異常,奇妙無倫,沒有壹絲余地可供回環,著著皆攻同敵人致命之處——只要壹擊便可致命之處!
於是,在不覺中,戰況又更加激烈,深沈而雄渾的勁力,在空中呼嘯縱橫,如壹道道含有壓力的閃電,是那麽懾人,又是那度尖銳!
瞬息間,又過去二百招了。
樹頂上的江青,憔悴的面孔上浮著壹層異樣的紅暈,他心中急想:“二人最後決勝負的時間,只怕就要到臨了,看情形,龍虎追魂束九出的功力,尚要較之君山獨叟高上半籌,束九山於三芝山下慘敗之後,這十余年來的瀝血苦練,果然沒有白費,倒是君山獨叟武功懈怠了……現在,若自已不由手分拒二人,則只怕要落個兩敗俱傷的局面!”
這時,君山獨叟裴炎忽然暴叱壹聲,手中“紅玉鎖骨鞭”倏而起如西天的殘霞,閃幻出條條燦爛的異彩,成弧,成線,成圈,成點,變化莫測的溜瀉向束九山身際的四方八面。
此乃為君山獨叟睥睨武林的“環光十八鞭”中之絕著:“流霞九絕”!
龍虎追魂束九山大吼壹聲,“龍虎雙矛”左右齊揮,兩臂急顫如浪,凝結成壹股股功力的寒芒,仿佛永不停息的交織而出,其中,竟尚含有壹絲絲淡淡的青色霧氣!
赤虹銀芒中,江青目光毫不稍瞬,意念在惱中急轉:“自已是否須要出手?但是,若下面這兩人同歸於盡,對自己可說是有益無害,兩人皆為自己之強敵,任是其中何人死亡,對自己也可減去日後壹患……而那君山獨叟若命喪於此,非但裴姑娘與二哥之事從此此可高枕無憂,更便自已免去應付靈蛇教報復的麻煩!”
他正在急速的動著腦筋,樹下已傳來兩聲瘋狂的吼叱君山獨叟的“紅玉鎖骨鞭”,正在“流霞九絕”的奇式中,幻化出條條流光,飛戳向束九山頸沿,前胸相連處壹十六處大穴,而龍虎追魂束九山的雙矛,亦有如長空的殞星,拖著精亮的曳尾,顫成點點,刺至君山獨叟下盤要害重脈!
二人的招式俱皆深奧精妙,狠辣無倫,在他們含怒施為之下,威力更是驚人,這彼此間拼命展出的奇招,已在瞬息間到達各人身前!
看情形,這壹下是難以躲避了,眼看著慘劇即將到來——幾乎在同壹時刻,快速得不可言喻,壹條瘦削的人影,閃電般自壹棵大樹的頂端飛下,當他身形帶起的第壹片雪花尚未往下墜落,壹片強韌的勁風,已如兩股有力的砥柱般,同激鬥中的二人逼去,於是——君山獨叟與龍虎追魂雙變驚呼壹聲,立即被那兩道強韌的勁氣,便生生地逼出五尺之外!
晶瑩的紅光,青白的寒芒,在剎那間斂逝,冷汗,亦自裴、束二人的額際滴落,他們知道,清楚的知道,彼此已自鬼門關打了壹轉回來。
往往,在人們激動之際,會將生命看得不值壹顧,但是,當他們冷靜下來的時候,則又會為自已當時的愚蠢而覺得可笑。
這原因很簡單,因為:凡是生靈,那有不愛惜自已生命的呢?縱然他會慷慨激昂地,視死如歸,究竟也只是壹時,而不是永久。
當二人驚魂甫定,愕然擡頭向那分開自已的來人望夫時,龍虎追魂束九山登時不由失聲大叫出來,“火雲邪者!”
這四個字仿佛四個巨雷,震得君山獨叟裴炎腦中嗡嗡作響,他張口結舌的註視著眼前這位形容憔悴,英挺俊逸的青年,幾乎不能相信,這即是目前痛挫教中數十高手,威摥四海五嶽的火雲邪者!
“他是怎麽來的?何時到達此處的?怎的自已竟全然不知?”君山獨叟有些驚棟的想著。
龍虎追魂東九山錯愕了半刻,忽然大叫道:“江青,久違了……閣下此來,是要幫誰的?”
束九山此言壹出,君山獨叟不由心頭壹震,面色連變,他知道自已靈蛇教與江青素來不和,大小沖突已不知有過多少次,而江青又忽然現身於此,莫不是有乘人於危之意麽?
裴炎緊張的退後兩步,緊握著手中的“紅玉鎖骨鞭”,雙目不敢稍瞬的註視著正向這邊緩緩行近的江青。
【完結】
文本大小:27957 字節